bitkeep钱包下载网址 > 正版imtoken下载地址 >
-
imtoken2.0下载 经济学的第4次范式转换仍在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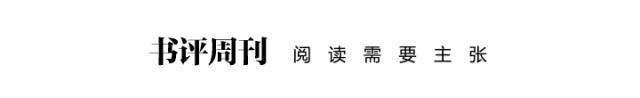
这是“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第4期imtoken2.0下载。
“经济学的每一次理论变革都将
通过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这两个阶段才能最终完成。”
——叶航:《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一个经济思想史的回顾和展望》,
《经济思想史学刊》2025年第1期,页2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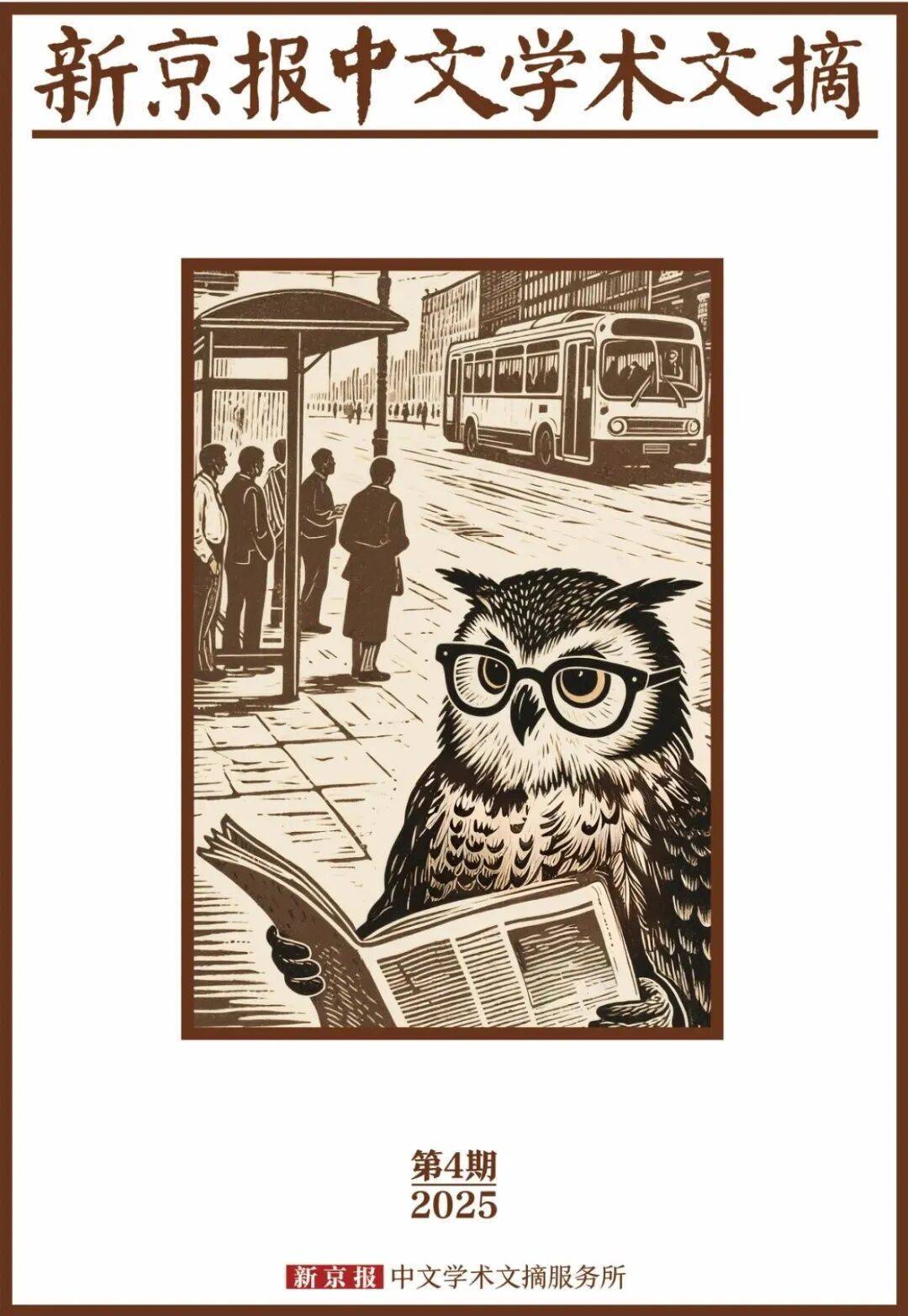
本期评议:刘守英 陈新宇
文本摘选:罗东
在当代,书籍之外,刊于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正在成为知识生产、知识积累的另一基本载体。《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的基础上试拓展“学术评议和文摘”这一全新的知识传播工作,筹备“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与期刊界,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刊物一道服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每一期均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评议人参与推选。每周五,《新京报》B叠报纸“书评周刊”摘选两篇论文,并在新媒体上转载全文。
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
此为第4期的第一篇论文。作者叶航回顾了经济思想在近现代的历次转变。在许多读者印象中,经济学最让人熟悉的是“经济人”“理性人”等科学假设,其实在经济学内部,如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持不同看法。由于经济学的数学化,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效仿自然科学最成功的学科。那么,托马斯·库恩基于自然科学而归纳的“范式转换”是否适用于经济学?作者认为有共通出处,即“转换”,也有社科的独特之处,即“综合”。经济思想一直在种种张力中辩证地演进。
以下内容由《经济思想史学刊》授权全文转载,有删减。摘要、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扫一扫,打开“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合集~
神仙姐姐刘亦菲,在荧幕前一直都以仙气飘飘的形象示人。然而在外媒镜头下,刘亦菲的生图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一面。眼前的刘亦菲脸蛋看起来比较浮肿,但是五官底子还是相当惊艳的,能扛得住外媒镜头的角度还能美成这样,真的不容易。
作者|叶航
纪录片《经济机器是如何运行的》( 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2008)画面。
前言: 库恩论科学发展与科学革命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是美国著名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的经典。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人类科学王国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库恩对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阐释并没有出现太大偏误,仍然是指导人们认识科学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库恩的科学哲学虽然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的,但用它来分析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规律,仍然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库恩认为,一个科学理论的发展大致会经历“常规”(normal)、“反常”(anomaly)、“危机”(crisis)和“革命”(revolutions)四个阶段(库恩,2012:8—18、44—55、56—65、79—93),它们的特征与属性分别如下。
《科学革命的结构》
作者:[美] 托马斯·库恩
译者:金吾伦 胡新和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新译本见张卜天译,北大出版社2022年7月)
科学理论处于“常规阶段”时,某一科学共同体内部已就解释该领域的现象达成一致共识和信念,这种一致的共识和信念被库恩称作“范式”(paradigm)。因此,所谓科学理论的“常规阶段”就是某种“范式”的确立并不断得到维护和发展的阶段。一旦科学理论进入这一阶段,该学科已经不需要为基础理论的每一个概念进行辩护,而科学家则可以把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探索相对艰深的问题上,以及致力于基础理论在实践中的推广和应用。
随着科学理论不断发展,人们或迟或早会发现一些无法被既有范式解释的现象,一开始它会吸引科学家努力把这些现象纳入原有的范式。但随着科学理论进一步推进,人们会发现有些现象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纳入原有范式。这时,科学理论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反常阶段”。那些不能被既有范式解释的现象被称为“反常现象”或简称“异象”(anomaly)。异象的出现标志着旧范式的根基开始松动,原有的共识和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怀疑。
随着反常现象不断积累,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最终意识到如果不扬弃旧有的范式,这种困境就无法得到改变。这时科学理论就进入所谓的“危机阶段”。库恩把“危机”看作新理论出现的曙光,因为科学理论一旦形成一个被所有科学家接受的“范式”,如果要宣告它无效,就必须用另一个新的、能被大家所接受的“范式”来取代它。正是在这种危机中,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得以酝酿和产生,直到最终诞生出新的范式和理论体系。
只有经历了“危机”的历练,科学理论才会为自己的新生迎来契机。科学理论的新生表现为范式转换,即用一个新的范式来取代旧范式。这时,科学理论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革命阶段”。科学革命的成功必然以废除一套旧的范式而代之以另一套新的范式为标志。因此,库恩特别强调,在科学革命的过程中,旧范式的废除和新范式的创立总是结伴而行的,科学家拒斥一个旧的范式,总是伴随着接受另一个新的范式。
电视剧《围城》(1990)剧照。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库恩创立的科学哲学中,“范式”这一概念具有贯穿全局的地位和作用,而“范式转换”则被库恩视作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的关键标志。因此,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也称为“范式革命”(paradigm revolution)。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发展之所以被划分为四个阶段,其重要依据就是人们对待“范式”的不同态度、不同立场和不同认知。
“范式”的英语paradigm一词来自希腊语paradeigma。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书中是在一种典型的、具有指导性的“范例”意义上来使用该词的(亚里士多德,1991)。因此,在该书拉丁文译本中,“范式”(paradeigma)被翻译成拉丁文“范例”(exemplum)。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英国著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其演讲和哲学著作中频繁使用“范式”这一词汇,从而使“范式”一词在英语世界受到了追捧。例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多次使用“语法的范式”(维特根斯坦,2005)这一提法。尽管我们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库恩使用这一概念时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但可以确认的是,库恩使用的“范式”一词,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与亚里士多德和维特根斯坦的传统有天壤之别。
在《结构》一书中,库恩所谓的“范式”是用来特指被某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公认为颠扑不破、不容置疑的基本认知、总体判断和核心论据。它往往以某种“公理”或“公理体系”的形式出现,并以由此演绎而来的一系列定理、推论或模型所组成。例如经典力学中的牛顿三大定律,相对论中爱因斯坦的能质转换公式,量子力学中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原理,等等。库恩还认为,“范式”不仅仅是某科学共同体内部用于开展研究所遵循的基本规范,同时还包括其成员开展研究所使用的技术工具或手段,如经典力学中的天文望远镜和电子显微镜,量子力学中的粒子加速器,等等(库恩,2012:36—43)。因此,一个科学理论的“范式”既是该学科认识特定事物的标准,也是该学科进一步实践和发展的基础。
以上介绍了库恩科学哲学的基本思想,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重要事实——库恩的这一理论主要是依据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归纳而来的,这与他青年时所受的专业训练高度相关。虽然在《结构》一书中,库恩也援引了许多天文学、化学、生物学和遗传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的例子来佐证他的理论,但对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是否符合这些结论,库恩自己在书中坦陈“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库恩,2012:12)。其实,我们不用苛求库恩,期待他跨出物理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边界,深入社会科学乃至经济学的世界。科学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有关科学本质最基本的认知和规律,尽管这些认知和规律只是来自某一具体学科,是针对某一具体学科实践经验的抽象,但它所具有的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性”仍然可以指导人们去认识其他学科发展的规律。
《科学革命的结构》早期英文版书封。
通过对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回顾,我们发现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库恩《结构》一书所揭示的自然科学具有相同的规律,即它的发展也会经历“常规”、“反常”、“危机”和“革命”四个阶段,而“革命”的本质特征同样表现为范式转换。但我们的回顾也表明,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还展现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规律,即经济学的发展是以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交替进行的形式实现的。这就意味着,经济学的每一次理论变革都将通过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这两个阶段才能最终完成。
下文将用四个部分分别阐述人类经济思想史上出现过的四次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以及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与经济学理论变迁高度相关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在这一基础上,本文再通过结语来探讨经济学的发展呈现不同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背后的原因。
经济学的第一次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一)经济学的第一次范式转换
经济学的第一次范式转换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这一转换的标志是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出版。在《国富论》中,斯密彻底颠覆了前古典经济学(preclassical economics)“财富管理”的研究范式,创立了古典经济学“财富生产”的研究范式,从而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实现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第一次大转换。
《国富论》
作者:[英] 亚当·斯密
译者:郭大力 王亚南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3年8月
我们把古希腊至中世纪的经济思想称为“前古典经济学”,它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约公元前387—公元前371年)为代表。“经济”一词在希腊语中的含义为“家庭管理”或“家政管理”。色诺芬认为,“财富管理也像医药、金工、木工一样,是一门学问的名称”,“一个懂得这门技艺的人,即便自己没有财产,也能靠给别人管理财产来挣钱”(色诺芬,1981:1)。从古希腊到整个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财富。只不过随着历史变迁,管理的范围逐步从家庭扩展到城邦,再从城邦扩展到国家。例如,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中拓展了“家政管理”的思想,提出奴隶主阶级必须研究城邦管理的“致富技术”(亚里士多德,1981:10—16);法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安东尼·孟克列钦(Antoyne Montchietien)则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第一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并将其定义为“国家如何管理经济的科学”(Montchietien,1615)。
事实上,在斯密以前产生过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一定程度上都是“财富管理”的践行者。著名的有英国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法国的弗朗索瓦·魁奈(Franois Quesnay)、苏格兰的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uart)。配第的经济学著作包括《赋税论》(1662)、《献给英明人士》(1664)、《政治算术》(1672)和《货币略论》(1682)等。作为一个由重商主义向古典学派过渡的经济学家,配第主张“一个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商业,特别是能使本国积累金、银、珠宝的产业”,为此他提出征收“累进税”和“消费比例税”等国家财政管理策略来防止货币流出国外(配第,1978:19—30)。从本质上讲,配第仍然是一个推崇“国家管理”的前古典经济学家。
魁奈是重农学派创始人,主要论著包括《租地农场主论》(1756)、《谷物论》(1757)和《经济表》(1785)等。作为重农主义者,他一方面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农业生产中有各种自然力参加工作”而“人是不能调节这些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的”;因此,魁奈主张用“开明的专制”和“道德秩序”来管理国家经济生活(魁奈,1979:333—408)。斯图尔特是晚期重商主义者,代表作是1300多页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论自由国家中对内政策的科学》(1767),被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称为“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马克思,1998:411—415)。该书对政府管理经济作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将“财富管理”范式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斯图尔特把政府管理经济的作用比喻成“工匠之手”(craftsman's hand),从而与斯密所谓的“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形成鲜明的对照(Steuart,1770)。
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彻底改变了经济学研究的轨迹,使经济学从前古典经济学的“财富管理”研究范式转向古典经济学的“财富生产”研究范式,从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纪元。从书名我们即可看到,斯密希望在这部著作中研究的问题是:国民财富的本质是什么,国民财富如何才能得到增加。这是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家从未认真研究过的问题,因为“财富管理”从本质上说只是面对既定的“财富”以及如何通过管理让这些既定的“财富”更好地发挥效用而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马克思,1974:376)
纪录片《经济学大师》(Masters of Money,2012)画面,从左至右依次为马克思、哈耶克和凯恩斯。
为了探寻国民财富的性质,斯密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所生产的所有商品都是国民财富,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从而既批判了重商主义所持有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源泉”的观点,也抛弃了重农主义所持有的“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的偏见,同时还与配第所持有的“只有生产金银制品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的错误看法划清了界限。
为了探讨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促使其国民财富增长,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篇“论劳动生产率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们的顺序”中认为,仅仅依靠管理、交换和分配并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只有通过“分工等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资本积累,从而增加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人数”才能促使国民财富的增长,并以此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在谈及分工时,斯密开门见山地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1972:5)为了说明分工怎样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斯密还特别举了著名的制针工场的例子,由于实行了分工,制针的效率提高了4800倍(斯密,1972:6)。现在,斯密的这些论断早已成为经济学常识,但在250年前它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思想。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1959:150)。
斯密的《国富论》为古典经济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全书共分为五篇,除上面提到的第一篇外,第二篇为“论资财的性质及其储蓄和用途”,第三篇为“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第四篇为“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第五篇为“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由此可见,《国富论》涉及的内容几乎包括了经济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它不但影响了其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包括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让·西斯蒙第(Jean Sismondi)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一大批新古典经济学家,比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等。
在这些人的经济思想中,我们或多或少都能看到斯密的身影。更令人惊叹的是,斯密在《国富论》所阐释的思想中,还包含着经济学未来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几大研究范式:比如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客观价值”研究范式,以“无形之手”所隐喻的“微观分析”研究范式,以“经济人”为表征的“理性分析”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范式几乎主导了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未来250年发展的路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马克思,1973:181)
(二)经济学的第一次范式综合
经济学的第一次范式综合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其标志是1848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学派的代表人物与继承者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以下简称《原理》)的出版。在《原理》一书中,穆勒将前古典经济学的“财富管理”研究范式与古典经济学的“财富生产”研究范式整合为一个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理论分析体系,从而实现了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研究范式的第一次大综合。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
作者:[英] 约翰·穆勒 [英]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译者:朱泱 等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4年12月
穆勒的《原理》一书,除“绪论”和“附录”以外分为五编73章:其中第一编为“生产”(共13章),第二编为“分配”(共16章),第三编为“交换”(共26章),第四编为“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共7章),第五编为“论政府的影响”(共11章)。从《原理》一书的内容结构看,前三编“生产”、“分配”和“交换”主要阐释了古典经济学“财富生产”研究范式所关注的基本问题;篇幅约占全书的70%,穆勒将其称为“经济学的静力学”(穆勒,1991:1—14)。后两编“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和“论政府的影响”是对前古典经济学“财富管理”研究范式的继承、拓展和升华,篇幅约占全书的30%。穆勒将其称为“经济学的动力学”(穆勒,1991:1—14)。
穆勒之所以要在古典经济学“财富生产”研究范式之外重新引入前古典经济学的“财富管理”研究范式,可以追溯至《原理》出版前4年他所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用的研究方法》。在这篇论文中,穆勒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讨论了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研究方法,可以看作他为写作《原理》一书所做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穆勒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经济学应该从人类行为最一般的假设出发推演出它的所有命题。而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假设有两条,第一是“对财富的追求”,第二是“对劳动的厌恶”。前者决定了人类必须通过生产劳动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后者则决定了人类又期望通过逃避劳动来获得不义之财;因此,经济学必须从这些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前者出发,构建相应的“财富生产”理论。从后者出发,则构建相应的“财富管理”理论。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实证研究来降低“由每个特例的复杂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Mill,1844)。荷兰经济学家弗洛里斯·霍伊克卢姆(Floris Heukelom)指出,穆勒是最早企图将经济学“公理化”(axiomatical)的经济学家(霍伊克卢姆,2020:10—12)。
《行为经济思想史》
作者:[荷兰] 弗洛里斯·霍伊克卢姆
译者:贺京同 赵雷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2月
正因为对经济学具有如上认知,穆勒与斯密所信奉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表现出很大不同。穆勒认为,不应该完全否认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管理和干预的必要性,因为“自由放任原则”假设个人都能对自身利益做出最好的判断,但事实上这一假设并不成立,特别是在涉及社会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场合(穆勒,1991:505—572)。据此,穆勒提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是必要的,并对其内容和形式做出了深入探讨。他认为,政府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可以干预经济生活:一是个人无法对自身利益进行判断的场合;二是个人需要帮助,但其他人不愿或不能提供帮助的场合;三是对社会福利有好处,但个人能力有限不能去做或不愿去做的场合。在此前提下,穆勒还认为,政府管理和干预经济可分为命令式和非命令式两种方式,而政府主要应该采取非命令式的方法对经济生活进行管理和干预(穆勒,1991:676—712)。
穆勒在《原理》中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在西方经济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且独特的地位。《原理》和斯密的《国富论》一样,都是20世纪以前流行时间最长、流行范围最广的经济学著作。穆勒对“财富管理”范式和“财富生产”范式的综合影响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和路径,即在其之后的经济学家,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学派,不论他们的立场是保守抑或激进,都会从“生产”与“管理”两个视角来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
(三)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经济学的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而经济学第一次范式转换始于18世纪70年代(以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于19世纪40年代(以蒸汽机的全面普及和应用为标志),而经济学第一次范式综合发生的时间也是19世纪40年代(以1848年穆勒《原理》的出版为标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经济学革命(包括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的两个时间节点刚好与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止年代高度吻合。由此我们不得不提出并思考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学的第一次革命与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时间上的一致性,究竟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或因果关系?
19世纪德国画家门采尔作品《轧钢厂》局部。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机器生产代替人力的时代,宣告了人类工业文明的诞生。而工业文明的诞生则彻底改变了财富创造的基本形态:在农业社会,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受到土地、河流和气候等自然力量的制约,社会财富的积累主要依靠对财富存量的管理才能实现。因此,以色诺芬等人为代表的前古典经济学思想将“财富管理”作为主要研究范式,正反映了工业革命前的人类经济生活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现实与社会实践。而工业文明的诞生则彻底改变了人对自然资源的被动依赖,使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实现财富的积累。因此,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从研究“财富管理”转向研究“财富生产”就成为一个历史的必然。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第一次转换事实上反映了以社会分工生产和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对以家庭协作和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革命性替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持续了80多年。在此期间,1807年,蒸汽机被成功运用于船舶动力;1814年,第一辆蒸汽发动机驱动的汽车诞生;1825年,第一辆蒸汽火车成功运行。蒸汽机在交通运输上的广泛应用有效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进一步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至1840年前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基本取代了传统经济的运行方式,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极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水平后,经济学家必然会发现“财富管理”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水平上协调生产、分配、交换和积累等经济活动,使经济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因此,将“财富管理”与“财富生产”结合在一起可以更全面地服务人类的经济生活,从而推动了古典经济学“财富生产”研究范式与前古典经济学“财富管理”研究范式的大综合。
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一)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转换
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转换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这一转换的标志性事件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颠覆了古典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客观价值”研究范式,提出了以边际效用论为代表的“主观价值”研究范式,从而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实现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第二次大转换。这一事件在西方经济学术史上被人们称为“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
《赋税论》
作者:[英] 威廉·配第
译者:马妍
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4月
(本文作者参考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配第是第一个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家,在《赋税论》中他写道:“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白银从秘鲁的银矿中运来伦敦,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配第,1978:48)。这表明配第在当时不仅认识到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而且还意识到货币的价值量也是由劳动量决定的。继配第之后,斯密和李嘉图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劳动价值论。斯密在《国富论》中不仅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1972:25)。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不但坚持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思想,而且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前提,他写道:“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李嘉图,1962:7)马克思对这一观点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认为李嘉图实际上指出了“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马克思,1962:5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的出版,则最终完成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化。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即把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种形式,并指出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则创造了商品的价值(马克思,2004:47)。劳动价值论以商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劳动量或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商品价值的衡量标准,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客观价值”研究范式。它是古典经济学研究价值的基本范式。
《资本论》
作者:[德] 卡尔·马克思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版本:人民出版社 2004年1月
与劳动价值论不同,边际效用论则将人的心理感受和满足程度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主观价值”分析范式。边际学派的先驱是德国的赫尔曼·戈森(Hermann Gossen),他于1854年出版了《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一书,提出了边际效用论的基本假设和定律。其中,第一条定律为“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那么这同一种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直至最终达到饱和”(戈森,1997:9),这条定律被称为“戈森第一定律”,也就是微观经济学中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第二条定律为“人们必须在充分满足最大的享受之前,先部分地满足所有的享受,而且要以这样的比例来满足:每一种享受的量在其满足被中断时,保持完全相等”(戈森,1997:16),这条定律被称为“戈森第二定律”,也就是微观经济学中所谓的“边际消费均等规律”;第三条定律为“每当成功地发现了一个新的享受,……都给人们提供了在现在情况下扩大生活享受总量的可能性”(戈森,1997:27),这条定律被称为“戈森第三定律”,也就是微观经济学中所谓的“创新收益增量规律”。我们可以看到,戈森近200年前提出的关于人类行为准则的假设,至今仍然是支撑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信条。
继戈森之后不到20年,许多经济学家都独立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思想和理论。它们包括: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于187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于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于1874年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因而被西方经济学术史称作“边际革命”。
但作为“边际革命”先驱的戈森,与大多数思想先行者的命运相似。1854年他自费出版了《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一书,在该书序言中戈森写道:“我相信,我成功地揭示了使人类能够相互发生关系并不断使人类进步的力量,而且大体揭示了这种力量作用的规律。像哥白尼的发现能够确定天体在无限时间中运行的轨道一样,我自信通过我的发现也能为人类准确无误地指明,他们为以最完善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所必须遵循的道路。”(戈森,1997:2)但该书出版后只卖出区区几册,而且毫无反响,于是他决定收回所有存书。
四年后,贫病交困的戈森于科隆病逝。因此该书长期不为世人所知,直到1888年才被柏林普拉格尔出版社重印出版。1879年,因提出“边际效用递减”而一举成名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偶然看到戈森的遗著,感到极为震惊,于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序言中对戈森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戈森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实在我之先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据我所知,他对基本理论的探讨比我更为综括,更为彻底。”(杰文斯,1984:18)
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第二次大转换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边际学派对效用和边际效用的研究扭转了此前古典经济学只关注生产、成本和供给的倾向,使经济学开始关注消费、效用和需求的研究,从而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准备了重要的理论资源;第二,边际学派的成员在分析效用和边际效用时,普遍使用了微积分和几何图形等数学工具,从而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及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数理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第三,边际学派提出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消费均等规律”和“创新收益增量规律”为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福利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功利主义哲学一起成为福利经济学的两大思想基础;第四,边际效用学派摆脱了此前的经济学(包括前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只研究社会经济主体的外部经济环境和经济利益关系的传统,第一次将研究视角转向人的内部、转向人的心理及其心理感受对行为的影响,从而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开启了破冰之旅。
(二)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综合
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综合发生在19世纪末,其标志是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研究范式与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观价值”研究范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从而实现了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研究范式的第二次大综合。
《经济学原理》
作者:[英] 马歇尔
译者:朱志泰 陈良璧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9年5月
在《经济学原理》(马歇尔,1981a,1981b)中,马歇尔一方面把古典经济学“客观价值”研究范式用来描述劳动价值和生产费用的理论改造成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供给”理论,另一方面又把边际效用学派“主观价值”研究范式用来描述效用和边际效用的理论改造成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效用-需求”理论,从而给这两个经典的理论传统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使它们焕发出新生。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还进一步通过“供给函数”及相应的“供给曲线”来刻画“生产-供给”系统的微观动态属性,通过“消费函数”及相应的“消费曲线”来刻画“消费-需求”系统的微观动态属性;并最终将它们统一于以数学(微积分)形式表达的“均衡价格”理论之中,从而完美地实现了古典经济学“客观价值”研究范式与边际效用学派“主观价值”研究范式的大综合。
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将物理学中的“均衡”概念引入经济学,创立了一整套分析方法。除了以上提到的“均衡价格”外,它还是马歇尔经济思想中最核心的分析方法,几乎贯穿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包括这一体系所涉及的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的全部内容。例如,当马歇尔论及消费的属性时,提出了“需求弹性”(demand elasticity)的概念,而需求弹性则取决于需求变动水平与价格变动水平的均衡状态(马歇尔,1981a:121—135)。当马歇尔论及生产的属性时,提出了“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与“边际收益”(marginal income)的概念,而生产的规模则取决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均衡状态(马歇尔,1981b:42—53)。
当马歇尔论及分配的属性时,将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生产要素”从三个扩展为四个,即在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所谓的“组织”(即企业家才能),并以此来说明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的来源——工资是劳动的价格,利息是资本的价格,地租是土地的价格,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价格;而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状态,利息水平取决于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状态,地租水平取决于土地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状态,利润水平取决于企业家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状态(马歇尔,1981b:179—322)。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虽然在结构上参照了穆勒的《原理》,但其逻辑的严密性、一致性和论述的清晰性却远远超过了穆勒。以至于经济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评价二人的著作时说,对于像马歇尔这样一位受过严格数学训练的经济学家来说,肯定无法忍受穆勒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所表现出来的模糊和粗疏(熊彼特,1965)。
马歇尔像。(沃尔特·史东曼1917年摄)
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是“研究范式”的综合,而且也是“研究方法”的综合。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不但继承和保留了古典经济学家宏大、深刻的叙事风格,而且还继承和发扬了由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等边际学派以及弗朗西斯·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人开创的经济学数学分析传统,最终于20世纪初形成了所谓的“数理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成为经济学理论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奠基之作,并使新古典经济学至今仍然被奉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马歇尔开创了经济学历史上的两个先例:第一,马歇尔是最先使用“经济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来命名其著作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评论此事时曾经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区别来比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熊彼特,1995:557);第二,马歇尔是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学教授,因为在此之前经济学在大学教育中都是从属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在马歇尔的不懈努力下,剑桥大学终于在1903年将经济学从人文学科中独立出来,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单独设立的经济系。
(三)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经济学的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及使用为标志),而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转换也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以19世纪70年代边际学派的兴起为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于19世纪末(以电力的普及和大规模使用为标志),而经济学第二次范式综合发生的时间也是19世纪末(以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研究范式第二次发生变化(包括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的两个时间节点与人类第二次工业革命完全同步。
荷兰画家梵高作品《夜间咖啡馆》中的电气运用。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电气化时代。经济学第二次范式转换发生在这一时期,反映了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以后,社会知识精英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新视野。边际学派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寻找人们对价值和效用的判断标准,开创了“主观价值”研究范式的先河。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个事实,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也是在19世纪70年代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数不是职业经济学家,比如戈森是律师,门格尔是记者,瓦尔拉斯在进入洛桑学院前一直从事文学期刊的编辑并出版过好几部小说。他们都是凭着自身的学术兴趣和对科学探索的热爱,在工作之余创立了边际效用理论。这也从侧面表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启,伴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使人们有更多闲暇时间来追求自己热爱和感兴趣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看,职业经济学家更容易受到传统理论的束缚和禁锢,从而更难进行理论创新。
第二次工业革命持续的半个世纪中,社会进步始终围绕着电力的应用展开。在此期间,发电机和电动机的成功研制拉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序幕。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等相继问世,让人类社会全面进入电气化时代,再一次使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都由一线工匠完成不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大多由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完成。这一事实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对科学的崇拜,在当时的英国和欧洲掀起了一股崇尚科学之风。这股风气对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综合产生了重大影响,马歇尔将物理学中的“均衡”概念及其相关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经济学第二次范式综合,既反映了人类工业文明处于相对鼎盛时期的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生活所产生的极大促进作用,也反映了现代科学理论的建构方式,imtoken钱包官方首页尤其是数学作为一种通用科学语言对经济学产生的重大影响,有力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公理化”和“数理化”的进程,从而成为经济学理论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标志。
经济学的第三次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一)经济学的第三次范式转换
经济学的第三次范式转换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这一转换的标志是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出版。凯恩斯在《通论》中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分析基点立足于厂商与个人行为的“微观分析”范式,确立了以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的“宏观分析”范式,从而实现了研究范式的第三次大转换,这一事件在西方经济学术史上被人们称为“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作者:[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译者:高鸿业
版本:商务印书馆 1999年4月
凯恩斯《通论》出版以前,新古典经济学家流行的“信念”是,任何商品过剩或商品短缺都是短期的、暂时的。按照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只要价格调整到位,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现象就能消除;因此从长期来看,只要市场价格机制不受干扰,供求之间的矛盾,包括商品市场的供求矛盾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总能够实现“市场出清”,从而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对此,凯恩斯在《通论》中创立了一套全新的、从经济总量出发的分析方法,试图否定他的老师马歇尔所建立的、只存在于“鲁滨逊漂流记”中近乎“乌托邦”的学说(凯恩斯,1999:25—26)。
凯恩斯首先提出“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的概念来解构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相等时的社会总需求,这一需求既包含了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也包含了生产者对劳动力的需求(凯恩斯,1999:28—32);但是,有效需求虽然是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的均衡点,但却未必是劳动力供求水平的均衡点,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即便在有效需求处于均衡状态的情况下,仍然可能无法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社会上仍然可能存在着大量“非自愿失业者”(凯恩斯,1999:52—57)。因此,凯恩斯给《通论》制定了两个目标:第一,揭示“有效需求”与“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第二,为政府解决失业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为了揭示有效需求和充分就业的关系,凯恩斯提出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指,在增加的收入中消费者用于消费的比例会趋向于不断减少(凯恩斯,1999:93—97);所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是指,生产者对生产同一产品的预期获利水平会随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下降(凯恩斯,1999:139—141);所谓“流动性偏好”是指,人们出于交易、预防或投机目的,总是希望保留一定数量可随时动用的现金货币的偏好(凯恩斯,1999:201—205)。
根据凯恩斯的分析,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一个国家总收入中转化为储蓄的部分会越来越多,如果这部分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则该国的有效需求就会萎缩,出现所谓的经济衰退(凯恩斯,1999:98—111)。但是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一个社会只有不断降低货币供给的利率水平,投资规模才可能不断得到扩大(凯恩斯,1999:141—150)。而由于“流动性偏好规律”的作用,银行利率不可能无限降低(凯恩斯,1999:205—216)。由此,凯恩斯得出结论:在三大心理规律共同发生作用的前提下,会导致一个国家有效需求的持续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则会降低社会的总收入水平,并进一步导致社会就业水平低下,从而产生严重的失业和经济衰退,乃至发生危机和萧条。
如上所述,在凯恩斯看来,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来自所谓的“三大心理规律”,它是人性中固有的行为倾向,无法通过市场的微观价格机制或利率机制得到纠正。因此,为了使社会摆脱失业和衰退的危机状态,必须从系统外部引入干预力量来管理有效需求,即由政府通过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便使总投资量等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储蓄水平,从而解决危机和萧条困境。为此,凯恩斯甚至提出“某种程度的全面的投资社会化将要成为大致取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凯恩斯,1999:39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避免经济再次陷入1929—1933年的大危机,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所建议的政策。例如,英国政府于1944年颁布了《就业政策白皮书》,规定政府必须维持足够规模的有效需求,以便使社会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美国议会于1946年通过的《就业法案》,把维持充分就业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目标(高鸿业,1999)。
凯恩斯所引领的经济学第三次范式大转换被西方经济学术史称作“凯恩斯革命”。作为一场“革命”,它不但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微观分析范式,而且还颠覆了自斯密以来一直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敬奉的“市场万能”的理念和信仰。它是对工业革命以来所建立的“自由放任”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反思与批判,并由此开创了“国家干预”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凭借《通论》一书,凯恩斯在西方已跻身于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家的行列,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被西方民众认为是可以与斯密、马克思、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相提并论的伟大人物。
(二)经济学的第三次范式综合
经济学的第三次范式综合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其标志是1947年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以下简称《基础》)一书的出版(Samuelson,1947)。在《基础》中,萨缪尔森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范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因此,萨缪尔森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作“新古典综合派”,从而实现了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研究范式的第三次大综合。
萨缪尔森创建的新古典综合理论旨在从三个方面对凯恩斯《通论》出版后给西方经济学造成的分裂状态进行弥补和缝合。
《经济分析基础》
作者:[美] 保罗·萨缪尔森
译者:费方域 金菊平
版本:商务印书馆 1992年9月
第一,是经济理论上的综合:以“充分就业”和“市场均衡”为界,把处于“充分就业”和“市场均衡”状态时的经济分析称为微观经济分析,也就是所谓的“微观经济学”;而把处于“未充分就业”和“非市场均衡”状态时的经济分析称为宏观经济分析,也就是所谓的“宏观经济学”;这种“理论综合”从本质上讲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拼凑”,但它却可以有效避免西方经济学因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导致崩溃的局面,并且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的“新凯恩斯主义”试图为宏观经济学建立所谓的“微观基础”预留了一个“入口”。
第二,是经济体制上的综合:在坚持私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对那些容易产生“市场失灵”和“道德风险”的部门,如邮政、公共交通、环保、军工、航天、保险等部门的全部或部分实行“国家所有制”,这就是萨缪尔森所谓的“混合经济”(萨缪尔森,1991:2)。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高峰时期国有经济占整个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度超过10%;8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的“私有化改造运动”,这一比重大幅下降,但至今仍占2%左右。第三,是经济政策上的综合:在坚持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特别是当经济运行出现明显的通胀、通缩、衰退或失业时,主张政府运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和调控,这就是萨缪尔森所谓的“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萨缪尔森,1991:509)。
1948年,萨缪尔森根据《基础》一书的内容体系,编写了一部供经济学专业大学本科生学习的教材《经济学》。该教材大约每3年再版一次,每次再版都会根据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更新教材内容。至2009年萨缪尔森逝世,已经更新到第十九版。到目前为止,《经济学》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销售总量超过1000万册。在西方世界,该教材被称为“经济学的圣经”,使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成为全世界流行最广泛的经济理论。
以萨缪尔森领衔的新古典综合派还包括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其中大多数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们的贡献主要有:希克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提出著名的“IS-LM模型”,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决定模型”与马歇尔的“一般均衡模型”结合起来,用来分析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Hicks,1946);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和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提出“哈罗德-多马模型”,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长期化与动态化,用于分析经济长期增长的条件(Harrod,1949);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结合起来,用来预测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Klein,1954);索洛(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索洛增长模型”,分析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Solow,1956);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微观金融和企业投资理论与宏观经济分析结合起来,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目标落实到实际应用层面(Tobin,1989);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证明了凯恩斯关于失业率和货币工资水平负相关的观点,从而用来指导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Phillips,1958);佛朗哥·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修正了凯恩斯消费函数只关注当前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系,从而揭示了长期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及短期消费波动的原因(Ando and Modigliani,1963)。
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对新古典综合派只是在形式上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拼凑在一起表示了不满,因此他们提出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的学术诉求,说到底就是意图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假设”的基础上重新解释和建构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例如,他们用“价格黏性”(price stickiness)、“菜单成本”(menu cost)、“工资刚性”(wage rigidity)等因素来解释凯恩斯经济学发现的市场非出清现象;用“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不完全信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货币中性”(monetary neutrality)、“预期判断”(anticipation judgment)等原因来解释凯恩斯经济学发现的经济波动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凯恩斯主义的学术努力,就是为了让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有机地、真正地融合为一体。
(三)大危机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经济学的发展
1929—1933年在美国爆发的大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经济学的第三次范式转换发生在1936年(以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为标志);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46年(以人类第一台计算机的问世为标志),而经济学的第三次范式综合则开始于1947年(以萨缪尔森《基础》的出版为标志)。经济学研究范式第三次发生变化(包括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的两个时间节点分别与大危机爆发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的时间高度重合。
以大萧条为故事背景的电影《明日之歌》(Make Way for Tomorrow,1937)剧照。
1929—1933年在美国爆发的“大危机”也称“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看上去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在1921年为67,1923年至1925年为100,1928年为110,到1929年6月则上升至126(Mcelvaine,1993)。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的股票市场突然出现了暴跌,拉开了大危机的序幕。危机迅速波及英国和欧洲,使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一幸免。
但是触发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事实上早已隐藏在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中。例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吉尔伯特(Charles Gilbert)指出,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已经出现“一个或几个社会集团支出减少的幅度超过了其他社会集团支出增加的幅度”(吉尔伯特,1986:699),而这种状况在英国也持续存在了多年,这正是凯恩斯在《通论》中分析过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事实上,凯恩斯在大危机爆发前已经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来讨论这个问题,如《货币改革论》(1923)、《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1925)、《给法国财政部长的一封公开信》(1926)、《货币论》(1930)、《劝说集》(1931)等。因此,大危机的爆发成为凯恩斯完成《通论》写作和出版的契机。大危机反映了人类工业文明由鼎盛转向衰退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及经济学理论产生的深刻影响,从而促使了新古典经济学“微观分析”研究范式向凯恩斯主义“宏观分析”研究范式的转换。
纪录片《二次大战启示录》(Apocalypse - La 2ème guerre mondiale,2009)画面。
被大危机打断的科学技术发展进程在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40年代末得以继续。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计算机的大规模使用拉开了机器代替人脑的序幕。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计算机的技术形态经历了真空管、半导体、集成电路和芯片四个发展阶段;而计算机的应用形态则经历了大型机房、个人台式、互联网终端和移动终端四个发展阶段,直至21世纪初开启了新一次技术革命。与此同时,经济学第三次范式综合则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末。在此期间,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常规”、“反常”和“危机”三个发展阶段,直至21世纪初开启了新的“范式革命”(本文将在下一部分详细介绍这一过程)。
经济学第三次范式综合与人类第三次工业革命基本同步这一事实,既反映了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恢复所带来的经济与科学繁荣对经济学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涌现出一大批像萨缪尔森、约翰·纳什(John Nash)这样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也反映了全球经济与政治中心由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向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转移,以美国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的经济理论替代了以英国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理论,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经济理论。
经济学的第四次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一)经济学的第四次范式转换
经济学的第四次范式转换发生于21世纪初,这一转换的标志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说,“传统上,经济理论依赖于经济人假设,该假设认为人的行为由自利的动机控制并且人们能够做出理性的决策,但实验结果表明,经济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假定需要修订,在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边缘地带展开的现代研究已经表明,某些概念如有限理性、有限自利和有限克制,是经济现象范畴后面的重要因素”。它表明曾经一统天下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分析”范式开始面临行为与实验经济学“非理性分析”范式的严峻挑战,拉开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第四次大转换的帷幕。
纪录片《经济学大师》(Masters of Money,2012)画面。
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个公理化的“理性人假设”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学模型计算所谓的最优效用,从而为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在内的经济主体提供决策的依据。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建构的“理性分析”范式,其逻辑之严密、形式之精致堪与物理学媲美,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但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却观察到越来越多无法满足“理性人假设”的行为异象,从而动摇了该理论的根基。
在相当长时间内,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认可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的发现。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行为的主体,而“非理性”只是一个随机现象。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没有问题,只要在模型中加入一个“误差项”(error term),就可以消除这类随机扰动。就像遗传学中用父母身高预测子代身高一样,虽然这种预测会出现意外,但模型的总体表现仍然非常优秀。因为只要误差是随机的,它们就会互相抵消(塞勒,2018)。但是,卡尼曼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却表明,人类在决策过程中普遍使用了一种“启发式”(heuristics)的思维模式(Tversky and Kahneman,1974)。卡尼曼认为,这种思维模式既不同于贝叶斯理性,也不同于有限理性;而是一种依靠人们的本能、直觉和情感的“非理性”决策方式,它在人类处理不确定事件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与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产生的偏离是一种“系统性”偏离,即这种偏离在给定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被预期和预测的(卡尼曼,2012:89—176)。
为了更好地理解第四次范式转换,有必要补充一个相关细节: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事实上由两个互相补充的研究规范所组成。其一是继承了斯密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传统,进而演绎出“理性人假设”并最终形成了“理性分析”范式,它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其二是延续了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的阐释,进而演绎出“均衡价格理论”并最终形成了“微观分析”方法,它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当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发起挑战时,一开始应该是准备同时颠覆这两个研究规范的,但1929—1933年大危机的爆发打断了凯恩斯的步骤,使他不得不将主攻方向放在对“微观分析”的批判上,这就使得“理性分析”范式向“非理性分析”范式的转换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不过在这半个多世纪中,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仍然没有脱离库恩对科学发展一般规律的阐释,新古典经济学“理性分析”范式在此期间完整地经历了“常规”、“反常”、“危机”和“革命”四个发展阶段。
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理性分析”范式的完善,它是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常规阶段”。在此期间,希克斯为“理性分析”范式创建了无差异曲线分析技术(Hicks and Allen,1934),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为“理性分析”范式建立了公理体系(冯·诺依曼、摩根斯坦,2004);萨缪尔森为“理性分析”范式奠定了数理分析基础(萨缪尔森,1992);而由热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和阿罗等人最终完成的“显示偏好理论”(Debreu,1954;Arrow,1959)则为新古典经济学“理性分析”范式的最终完成落下了收官之子。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作者:[美] 冯・诺伊曼、[美]奥斯卡·摩根斯顿
译者:王宇 王文玉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12月
但出人预料的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完善了“理性分析”范式的新古典经济学非但没有就此一路高歌猛进,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强势崛起,“理性分析”范式却不得不面临日益增多的“异象”挑战,从而使新古典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反常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此期间,为了弥补“理性分析”范式频频出现的漏洞,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创立了“信息经济学”,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构建了“拓展的效用函数”模型,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则提出“有限理性”模型。这些努力事实上都围绕着同一个学术目标,就是试图在“理性分析”范式可以接受的框架或范围内为新古典经济学碰到的种种“异象”进行辩解。
但从20世纪80年代直至20世纪末,经济学家发现“异象”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而为其辩解的难度也越来越高,这使得主流经济学家不得不采取沉默的态度来坚持他们的主流立场(叶航、汪丁丁、罗卫东,2005)。根据库恩的理论,这些特征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危机阶段”。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新创办的《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专门开设了一个介绍“异象”的专栏,并邀请芝加哥大学行为决策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该专栏到20世纪末一直延续了近20年,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思想史上又一次范式转换,即发生于21世纪初的经济学第四次范式转换,使经济学进入一个所谓的“革命阶段”。
《“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
作者:[美] 理查德·塞勒
译者:王晋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6年1月
(二)经济学的第四次范式综合(展望)
经济学第四次范式综合目前虽然还在酝酿之中,但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却可以对第四次范式综合的形式做出一个大致的推断和展望。经济学的发展以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交替进行的方式实现,而每一次范式综合都将前一次转换前后的两个范式融合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如果经济学第四次范式转换是从“理性分析”转向“非理性分析”,那么经济学第四次范式综合就应该将“理性分析”和“非理性分析”融合于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
这一综合的理论框架我们不妨以“行为人假设”称之,但不论它的名称是什么,作为一个新理论的逻辑起点,“行为人假设”的内涵大致可以表述为:人的行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统一体。
“行为人假设”的主要依据是近年来在认知心理学和决策神经科学中广泛流行的“双系统模型”(dual system model)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受制于两套不同的决策系统:一是基于“启发式”(heuristics)的分析系统,通常被称作“系统1”;二是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通常被称作“系统2”。系统1的运行主要依靠我们的本能、直觉或情感;而系统2的运行则依靠我们的计算、推理或权衡(卡尼曼,2012:3—81)。其实,关于“双系统”决策的思想在经济学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凯恩斯关于“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的投资理念(凯恩斯,1999:137—150)、熊彼特关于“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的论述(熊彼特,1991:64—105),以及奈特关于风险、不确定性和企业家利润来源的探讨(奈特,2005:147—171)。他们认为,在常规经济活动中,“理性”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在投资、创新等高度不确定情境下进行决策,仅仅依靠“理性”判断往往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在更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人类所固有的直觉、冲动、血性和勇气。
演化神经科学(evolutionary neuroscience)认为,人类思维模式的上述区别来源于大脑的进化。而大脑进化是一个跨越物种的生命奇迹:距今6亿年左右,神经组织神经元(neure)和神经胶质细胞(neurogliocyte)出现在无脊椎动物或软体动物身上;距今4亿至5亿年左右,神经系统包括大脑和脊髓开始出现在脊椎动物或节肢动物身上;距今2.5亿至4亿年左右,大脑特化(hemispheric specialization)即大脑左右半球的分工开始出现在爬行动物或两栖动物身上;距今2亿年左右,大脑新皮层(cerebral neocortex)开始出现在哺乳动物身上,从而开创了“理性思维”的曙光;新皮层特别是它所包含的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是大脑执行高级认知功能,如计算、推理、语言和学习的专属脑区。人脑新皮层是所有哺乳动物中最发达的,与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相比,面积大了三倍,拥有的神经元数量多了两倍(Herculano Houzel,2009)。因此,人类成为地球的万物之王,创造出辉煌的文明是有其深厚物质基础的。
但是,大脑进化的底层逻辑在于,在生物大脑进化的每一个节点上,新的功能都是在旧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增添某些“部件”来实现的。用法国分子生物学家、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的话说,“进化是一个修补匠,而不是工程师”(Jacob,1977)。这意味着,进化并没有“格式化”大脑原有的组件和功能,我们“理性”的脑区与“非理性”的脑区以并行模式存在并发挥各自的作用(Linden,2007)。从经济效率角度看,“理性”行为主要用来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往往是高等生物(主要是灵长类)面对没有先例的事物时采取的神经反应模式,这种反应包括信息识别、信息判断、信息处理等多个环节,其能量消耗要远远超过以本能、直觉或情感触发的行为,如果所有行为都采取这种方式,反而是不经济和无效率的(叶航、汪丁丁、贾拥民,2007)。因此,我们会发现,一方面,人类保留了大多数依赖本能、直觉和情感触发的行为,只在这些行为无法解决问题时才调动更高阶的“理性”行为;另一方面,人类会通过学习和训练,不断把一些具有重复性的行为从需要调动“理性”的行为变为只需要依靠本能和直觉的行为,如运动员、乐器演奏家和高级工匠的行为。以至于美国著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人比动物智慧是因为我们的本能比它们更多,而不是更少”(James,1890)。
《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2001)剧照。
从演化神经科学的视角看,人类大脑和心智中“非理性”和“非自利”的行为偏好,其实是那些有益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行为规范”或“社会规范”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内部化”(internalization)的结果。那些具有重大生存价值的应对策略会以“本能”、“直觉”、“情绪”或“情感”的形式内化为我们大脑的某一神经机制,这种机制在特定的情境再现时将会被激活,从而指导我们去正确地行动。比如恐惧、厌恶、悲伤、愤怒以及公正、友好、爱护、信赖等,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帮助我们迅速做出决断,使我们保持警觉、远离危险、摆脱困境,让我们彼此信任、互相帮助、团结协作。正是这些机制构成了行为经济学家今天所揭示出来的大部分所谓“非理性”“非自利”行为异象的生理、心理和神经基础。而在人类演化过程中较晚近才形成的大脑新皮层,以及它所具有的被我们称作“理性”的推理、计算和权衡功能,说到底只不过是为了让上述机制能够更好地、更精致地发挥作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大卫·休谟(David Hume)那句经典的名言:“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休谟,1980:453)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片面强调人类心智中“理性”的一面,虽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它的解释力捉襟见肘就不足为奇了。而行为经济学的学术目标是将“理性分析”范式与“非理性”范式融合于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从而使传统研究范式能够解释的现象在新的理论框架下仍然可以得到恰如其分的解释。而传统研究范式不能解释的现象,比如众多的行为“异象”,在新的理论框架下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行为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根据这一目标所描绘的前景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从而最终完成经济学的第四次范式综合。
(三)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经济学的发展(展望)
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于21世纪初(以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应用为标志),而经济学第四次范式转换开始的时间也是21世纪初(以2002年卡尼曼和史密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我们看到,经济学第四次范式转换与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基本在同一时间拉开帷幕。
如果说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一个“人的体力”被逐步替代的过程,那么第三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一个“人的脑力”被逐步替代的过程。不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对脑力的替代是通过计算机硬件系统放大人脑计算功能实现的,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脑力的替代则是通过神经网络软件系统放大人脑学习功能实现的。就替代“人的脑力”而言,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前者对人脑的替代是被动的,即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CPU)只能根据人类给它制定的运算规则或逻辑规则来进行工作;而后者对人脑的替代则是主动的,即计算机的工作是根据神经网络模型的自主学习功能不断进化迭代完成的。这就是我们仅仅把后者而不把前者称作“人工智能”的原因。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1)剧照。
经济学第四次范式转换开启了“理性分析”向“非理性分析”的转变,就人类的决策行为而言,这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但对这两种不同模式的理解可能远远超乎人们的预想,对人类的大脑来说,“理性”是一种被动的决策行为,而“非理性”才是一种自主的决策行为。
这是因为,理性决策通过计算、推理或权衡来进行工作,而计算、推理或权衡的规则却是外部给定的。例如我们通过数学定律进行计算,通过逻辑规则进行推理,通过期望效用原理进行权衡。非理性决策则通过本能、直觉或情感来进行工作,而本能、直觉或情感却是我们大脑的神经网络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迭代形成的。在人工智能的工作环境下,神经网络模型的进化迭代往往只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能完成。像ChatGPT发布不到两年,就进化迭代出四个版本。因此,神经网络模型被称作人工智能的灵魂。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人工智能的实现得益于人类神经网络的启迪,而神经网络模型的实践又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而这种科学进步的结果必然会对经济学的第四次范式转换产生深远的影响,使经济学家更好地认识神经网络的运行机制,从而在此基础上更全面理解并阐释“非理性分析”范式的本质属性。正因为如此,在第四次范式转换过程中,经济学与神经科学结盟产生了“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叶航、罗俊,2022;叶航、汪丁丁、贾拥民,2007)。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发展在经历了内容搜索和内容推送后,现在已进入一个内容生成阶段,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实现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从而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人工智能对人脑更全面的替代。人工智能的这一发展趋势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建立在各种不同神经网络模型上的软件系统加以实现的。但其发展潜力已经受到算力的严重制约,而算力的大幅度提高则必须进一步依赖高端芯片及其产业链、数据存储设备、公共算力平台甚至电力保障系统等硬件设施的全面发展。
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终完成还将依靠软件系统与硬件系统的协同进步和不断迭代。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看,第四次范式转换中出现的“非理性分析”范式也必然与“理性分析”范式取得深度的融合与协同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再一次大综合。这一综合将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人类自身,包括人类的大脑和神经元链接网络,以及人类的认知、决策和行为,从而让经济学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结语: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上文的阐述和分析表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发展过程与库恩在《结构》一书所揭示的自然科学具有相同的发展规律,即经济学的发展也会经历“常规”“反常”“危机”和“革命”四个阶段,而“革命”的本质特征同样表现为范式转换。但通过经济思想史的回顾,我们也发现了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发展规律——经济学的发展是以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交替进行的形式实现的,而每一次范式综合都是将前一次范式转换前、后的两个“范式”融合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
可以将本文所述的全部内容,即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所催生的经济学发展历史的轨迹,以一张浓缩的简图表示,见下图。
科学技术进步下的经济学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果认真考察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也是以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的形式完成的,只不过自然科学的范式转换(范式革命)与范式综合是同时完成的,即每一次范式转换的实现就意味着一次范式综合的完成。例如,在物理学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五次理论“大革命”,而这五次理论“大革命”也意味着物理学理论同时实现了五次范式“大转换”和五次范式“大综合”。
物理学的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7世纪80年代,其标志性事件是“牛顿经典力学”的诞生。在牛顿经典力学之前,研究天体运动规律的天文学与研究一般物体运动规律的物理学是两门完全不同的科学,但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的统摄下,天体的运动和一般物体的运动都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从而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一次“大革命”,即研究范式的第一次“大转换”和“大综合”。
物理学的第二次革命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其标志性事件是“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的发现。在“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发现以前,物理学中各种不同的能量都以独立的形态出现而被不同学科所研究,而“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则揭示了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之间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联系,从而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二次“大革命”,即研究范式的第二次“大转换”和“大综合”。
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其标志性事件是詹姆斯·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电磁场理论”的诞生。在“电磁场理论”诞生前,电、磁、光都是作为不同的物理现象被分别研究的,但麦克斯韦通过四组方程式揭示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联系,实现了电、磁、光的统一,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电磁波的研究和应用,从而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三次“大革命”,即研究范式的第三次“大转换”和“大综合”。
电影《爱因斯坦与爱丁顿》(Einstein and Eddington,2008)剧照。
物理学的第四次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其标志性事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相对论的出现颠覆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石——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揭示了时间、空间和物质运动之间的统一关系。事实上,牛顿经典力学只是对宏观物质低速运动属性的描述,相对论则是对微观物质光速运动属性的描述。相对论的诞生将牛顿经典力学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其中,从而完成了物理学的第四次“大革命”,即研究范式的第四次“大转换”和“大综合”。
物理学的第五次革命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性事件是“波粒二象性”(wave particle duality)理论的提出,成为支撑量子力学的重要基础。“波粒二象性”理论认为,电子和光即一般物质在微观层面同时具有波动和粒子两重属性。这就意味着经典理论对“波”与“粒子”的描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加以实现,从而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五次“大革命”,即研究范式的第五次“大转换”和“大综合”。
物理学与经济学在范式转换和范式综合实现形式上的区别,事实上反映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身的学科区别。因为,自然科学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所揭示的规律一般通过数学模型来加以呈现,判断标准比较客观和直接,新旧理论范式之间的属性和关系往往一目了然。因此,更容易被人们发现,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社会科学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所揭示的规律往往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冲突。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每一次理论上的范式转换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社会实践才能被人们逐步认识并普遍接受,进而才能形成共识并酝酿出新、旧理论之间的综合,从而拉开了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之间的时间距离,使范式转换和范式综合成为理论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文献出处】 叶航:《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一个经济思想史的回顾和展望》,《经济思想史学刊》2025年第1期,页21-54。
本文内容由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摘选。作者:叶航(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本期评议: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新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文本摘选:罗东;编辑:西西;导语校对:薛京宁。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imtoken2.0下载
